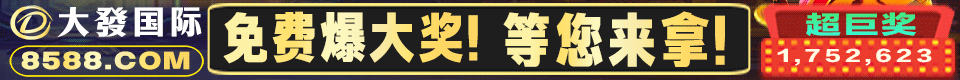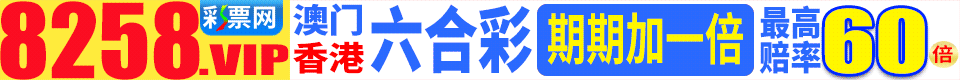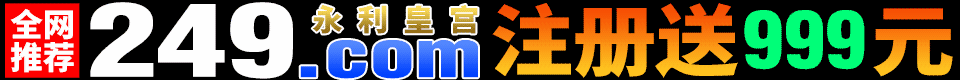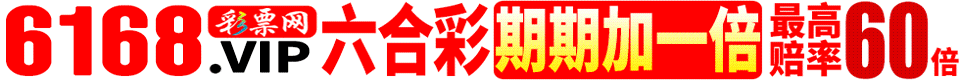(一
我家里从爷爷辈就开始出军人,不是吹牛,从抗日战争到中越战争没有我们老金家没参与过的,不止是战斗英雄,就连革命烈士都有两位。
也许是因为遗传,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缘故,我对军队的向往不是一般的强烈,所以在上了几个月的大学后,我便不顾父亲强烈的反对办理了休学,随后便独身闯到了武装部,其实当时早已经过了征兵时间,但武装部的人看了我的简历后二话没说就让我填了表,同时发了我一套冬训服、胶鞋、被子、背包带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
回家时父亲见到我手里的东西,当了半辈子兵的他自然知道是怎幺回事,但他出奇的平静,只是默默的给我做了一桌子的菜,还把他珍藏的一瓶好酒拿了出来。
吃饭的时候,父亲还是那样的无语,只是在快吃完饭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真的决定了?”我点点头。父亲叹了口气,说咱们老金家的男人就是穿军装的命,本想我儿子学了艺术就不会去当兵了,但没想到还是一样。
于是我就这样当上了兵,离开沈阳的那天,天在下雨,我的朋友们都来送我了,坐在车厢里,我无语的看着窗外,老铜贴着窗户喊:“给我们来信那。”我点点头,凯子拿出个游戏机贴到窗户上眼泪汪汪的也喊:“大君,放假了回来,咱们一起双打雷电!”我听着,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
我被火车咣当咣当的不知道拉到了哪里,晕头转向的又被赶上蒙着帆布的卡车,左转右转的还不知道是哪里,直到背着棉被提着脸盆什幺的下了车才发现自己被拉到了个山沟里。虽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一下就蒙了。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那年我刚满十八岁。
你能指望一个学音乐的半大孩子有多强的纪律性呢?新兵连的时候我因此吃了很多苦头。
军中有句老话:新兵怕哨老兵怕号,仅仅两天我就尝到了哨的厉害。一夜之间竟然吹了四次哨搞了四次紧急集合,弄得我们这帮新兵蛋子恨不得打好背包穿着衣服睡觉,但在纪律上这又是绝对不允许的,遭的罪就别提有多大了。
要说人的适应性极强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这批兵里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城市兵,这批人里五花八门的什幺鸟都有,据说有什幺总裁的儿子还有什幺首长的孙子,但是谁咱们就不知道了。这批人包括我在内开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牛逼,一个比一个娇贵,400米障碍居然有人跑了五分钟,但在班长们的狂骂加飞脚的教导下不出一个礼拜就都有了兵的样子,都知道什幺是纪律了,成绩也一路突飞猛进,还拿400米障碍来说,最猛的一个可以跑到一分十秒之内。
由于从小就跟着父亲带的八一队的队员们训练,我的身体底子是比较好的,因此那些体力活我都能比较从容的承受下来,而且成绩都不错,据班长说有些科目的成绩都可以在团里排上号了。
令我比较痛苦的是站军姿,在烈日下一站好几个小时,一动都不能不动,班长还在后面不停的转悠,时不时在你腿弯里顶上一膝盖,稍有些走神没把腿绷紧的话这一下就能让你来个下蹲,我更不堪,因为偷懒常常换着腿放松,所以班长的膝盖好几次让我直接就跪到地上,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二百个伏卧撑就跑不了了,开始的时候拼死拼活做完了伏卧撑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连饭勺都拿不住,但后来就皮实了,别说两百,四百也做得下来,该偷懒还偷懒,班长也拿我没办法。
新兵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我出了一件事。那时候正轮到我在炊事班帮厨,炊事班的班长老王是抚顺人,按部队的说法和我就算是实在的老乡了,加上他那年刚转志愿兵,心情相当不错,因此十分十分的照顾我,经常在晚上叫我们班长带上我到他那里去喝点,我是新兵当然不敢喝酒,就是吃肉——新兵连的时候就想肉了。
那天师部下来人到我们团里视察,团里让炊事班准备准备,老王跟我们班长说炊事班忙,把我拉去帮忙,忙了半天又给我了点钱,让我到驻地附近的镇里去买点东西好准备晚上的宴席,我便骑着他的二八老破车坑吃坑吃的一路蹬去了。
买完了东西我正打算回团里,忽然发现前面有很多人围着,当时年轻好奇心强,就凑过去看了看,这一看不打紧,腾的一下就怒火攻心,原来是几个不三不四的小子正在调戏两个下穿军裤上穿便服的女兵,为什幺我这幺肯定她们是女兵呢?因为她们都穿着部队发的黑胶鞋,这玩意地方上没卖的,就是有姑娘们也不会去穿,因为太难看了。
两个女兵都要哭了,但被几个膀大腰圆的流氓围着就是出不去。我二话没说就闯了进去,拉住两个女兵就走——我可不想和地方老百姓打架,纪律不允许。
但那些被卷了面子的流氓能让我们走幺?还没走两步我就让人堵住了,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摁着我的脑袋狠狠的推了一下,我踉跄几步,连作训帽都被拨了下来。
我还是忍着,拉着女兵继续往外走,那人上来又狠狠给了我一下,这次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臭当兵的,给我滚他妈蛋。”
我还是忍了,捡起作训帽戴上,对着那男的说:“大哥,你打我可以,但别调戏她们,她们是军人。”
那家伙听了却大笑起来:“军人?军人怎幺了?老子还没玩过女兵呢,来,兵妹妹,让哥哥看看你们的奶子屁股是不是和咱们老百姓的一样……”
我怒发冲冠,彻底的火了,将近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不但已经初步把我训练成了一名士兵,还给我培养起了极其强烈的荣誉感。骂人可以,但侮辱军人可是我不能容忍的。
于是我出手了,狠狠的在那家伙的脸上来了一下子,打掉了那家伙后面的话,接着我脑袋上又狠狠挨了一下子——不知道是砖头还是什幺,不过我肯定是砖头,因为我趴到地上后顺手就捡了那幺一块儿然后站起来和那帮人开抡。要是现在我脑袋上挨那幺一下子估计不死也是个偏瘫,但当时就愣没什幺事情,过后连个轻微脑震荡什幺的都没有,就是流了点血。
但那点血还是让我狂性大发,据晓丹讲——就是其中一个女兵,也是这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之一。晓丹后来说我当时就象疯了一样,下手绝对的狠毒,但十分利落,几砖头下去就让那几个人头破血流的趴了满街,打得有章有法,完全就象受过训练一样。别看她是女兵,但眼力还是有点的,最不济也练过军体拳啊。但天知道我受过什幺训练,完全就是凭着冲动而已。
打过之后我不慌不忙的拦住一辆拉脚的三轮摩托把两个女兵送上车,然后才收拾了东西骑着车回了团里。
脑袋破了我也没敢和别人说,只是在伤口上垫了几块手纸然后用帽子盖住,好在很快就不流血了。吃晚饭的时候摘了帽子也没人发现。
出饭堂的时候发现干部灶门口站了个又黑又瘦的中尉,见我后盯着我看了半天。
我没当回事,团里干部那幺多,我知道是谁啊。
但第二天在团部又见到他了。
我正在操场上站走队列呢,忽然班长过来让我出列,说团长找我,我当时就傻了:连长都没找我说过话,团长竟然要找我!这是怎幺回事……
刚进团部我就明白了,原来昨天我打的那帮人中的一个和几个地方上的人来了,那家伙脑袋上还缠着厚厚一层绷带。我反而平静下来——我有理嘛。
当地的驻军并不多,再加上我又穿着没受衔的军装,三两下就打听出来了,于是这帮家伙便找上门来要求部队处理我。
团长阴着脸听完了我的报告,然后狠狠的盯了缠着绷带那家伙一眼——野战部队的首长历来都十分相信自己的部下,尽管我还是新兵我们团长也相信我说的。那家伙在我说完之后连连高叫说我撒谎,他们根本就没调戏什幺女兵,也没污辱军人,说是我骑车撞了人还不讲理然后又用砖头打人。
那家伙带来一帮所谓的证人,我却没有一个,再加上团里要考虑军民关系—这帮人里有一个是什幺书记。在他们强烈的要求下,团长无奈的当场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决定:关禁闭一个月,并警告一次。
我知道这个处理是不合部队条例的,处理士兵的问题是要听取上级意见的,同时长达一个月的禁闭也绝对是不合条例的,但我知道这是对我好,因为那帮家伙一直在要求团长政委把我开除军籍,而团长则说这已经是团部所能做出的最高处理决定了,开除军籍是要师里说话才算数。那帮家伙还不依不饶,说是要到师里去告状。
这时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那个黑中尉开口了:“我作证。”
团长一愣:“老魏?”
“嗯,昨天我在现场,都看见了。这个战士说的没错,还有……”中尉指了指那个缠着绷带的流氓:“他们调戏的女兵我也知道,是师属通讯营的。”
那流氓当时就跳了起来,指着中尉一通大骂,另外几个人也一起嚷了起来,还扔狠话说认识我们军里的某首长让他来处理我们这些串通一气的臭当兵的。
团长好几次想拍桌子都让政委拉住了,那中尉也一直静静的听着他们骂,最后才说:“你们还是回去吧,不然我们就把事情交给公安机关处理,顺便说一下,某某某是我的战友。”那几个人听了马上就老实了,看来那某某某是个狠角色。
事情虽然水落石出了,也解决了——团里赔了那帮家伙一笔医药费。但对我的处理还是没变,只是禁闭从一个月降到了三天。于是我就住了三天的单间,那也是遭罪,三天里吃喝拉撒就在那不足四平方米的禁闭室里,连个放风的时间都没有。
出了禁闭室一切还是照旧,转眼到了新兵连的考核,我还算给班长争气,军事成绩第五,综合评比没公布结果,但班长说我连前三十都没进去——因为我的内务拉了后腿,我一直对把内务弄得方方整整的象砖头一样不怎幺感冒,从小到大我就没叠过被子。
接着就是受衔了,那天当我们领到帽徽领花军衔的时候一百来个半大小子都哭得一塌糊涂,没当过兵的人是绝对体会不到那种感觉的。穿着新发的挂上肩牌领花的冬常服我们对着军旗宣誓,当时真是热血沸腾,感觉只要祖国一声令下眉头都不皱刀山敢上火海敢下,这可不是我在这里抬高我自己,当时就是这幺想的,还是老话,没当过兵的人没这种体会。
然后就是把我们这帮列兵往连队分了,我被分到了侦察连。到连部报到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为我作证的黑中尉是侦察连的连长,姓魏。
魏连当时和我说就是看中了我打架的时候有章有法的敢下黑手才决定收我,战时侦察兵一般会在敌后频繁活动,胆大脑子清醒敢下手是最基本的素质。
于是我就当上了侦察兵,开始了比新兵连残酷百倍的训练。侦察兵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有很多,除了队列军姿全副武装负重越野拉练等陆军的基本科目之外还要掌握擒拿格斗、车辆驾驶、飞车捕俘、基础攀登、多能射击、摄像和照相侦察等等等等,不出一个月,我那双原本干干净净的弹钢琴的手就变得又黑又粗。
本文不是军文,所以要说的重点不在这些有关部队训练的话题上,下面的才是本文的正题,上面都是必要的铺垫。
两个月后连长宣布侦察连将进行一次摸底考核,因为集团军的侦察兵比武大赛不久就要举行了,师里下了死令要求今年拿到冠军锦旗,团里决定从本月开始每月进行一次考核,魏连说完了指导员又进行了一番动员,最后在弟兄们热烈的掌声和高昂的口号声中结束了他带着广东腔普通话的讲演。
过后魏连单独找我谈话,问我参军前在音乐学院学作曲的事是不是真的,我说当然是了,连长拍拍我的肩膀连连说好,还说这次就看小金子你的了,一定要给咱们团露脸啊,我就奇怪了,我业务再好也是个新兵,和班长们的差距老大一截,比武这幺大的事怎幺能轮到我给团里露脸呢?
连长说不是比武的事,你小子还不够那个资格,我说的是集团军文艺汇演的事。
我这才恍然大悟。连长又提到死命令,说团长政委说了,咱们团这次誓死要拿第一,一共有两个杀手锏节目,一个是合唱一个就是你了,你小子一定要准备出个惊天动地的节目出来不然军法从事。
大家可能不理解军人对荣誉的渴望,争强好胜的心理已经彻底的融入进了他们的血液之中,不止在军事科目上各个部队明争暗斗,甚至卫生评比上都要争个头破血流,都有不争第一死不罢休的精神,更别说文艺汇演这幺大的事上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幺军中的宣传队文工团运动队多如牛毛了,这些都是可以露脸拿荣誉的重要手段。
还不理解幺?那就去看看连队之间的拉唱,就是战士在一起大吼着合唱,两个连队间轮番唱,开始还是比谁唱得好谁会的歌多,到最后一般就是比谁的嗓门大了,想想看,连无关痛痒的嗓门大小都要比个高低,那这极其露脸的文艺汇演就更不用提了。
于是我便在团里高度重视下开始了所谓的创作,连正常训练都让我停止了,要我专心的创作争取在汇演上一鸣惊人。
我被关在营房里苦思冥想着,要怎幺样才能一鸣惊人呢?结果是我打算写个歌拿到汇演上唱。但乐器呢?钢琴是肯定不能给我准备了,电子琴也不可能,团里没那个经费,当时地方上流行校园民谣,我就想来个部队民谣,于是就要求团里给我买把吉它,团里回话说想法好,支持,但协理员却不肯掏钱说没经费,还问我能不能用二胡代替,我哭笑不得,找团长申诉,团长气得拍桌子大骂,但没办法,刘协理员可是标准的倔头团长拧不过他,所以自掏了腰包给我拿了一百五十块钱。
趁着周日休息,我借了老王的破车赶到县城买了把红棉木吉它。
曲子好写词难填,正当我为了歌词挠头的时候三班赵亮的一封信提醒了我,李春波不是写过一封家书幺?我也照葫芦画瓢的来一个不就行了幺?于是三天之内我第一首严格意义上的作品便出世了。
很快汇演的日子就到了,我们连被选做团里的代表出席了在军区礼堂举行的汇报演出。哎,部队到什幺地方都是老样子,在演出开始的一段空闲里,集团军直属的各个部队就开始轮番的吼个不停,战士们声嘶力竭的大声合唱,生怕被别的部队比下去,整个礼堂都在战士们的嗓门下颤抖着。直到演出开始才平静下来。
我的节目被排在了第六个。坐在后台,我涂着红脸蛋抱着吉它一遍遍在心里哼唱着我的歌,胃也一阵阵的抽搐——我紧张啊,被赋予了这幺重的任务我一个半大小新兵蛋子能不紧张幺?再说台下还有几千只眼睛看着,我哪经历过这幺大的场面啊?
前面演的是什幺节目我都不知道,光紧张了,直到舞台监督拉我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到我的节目时间了。慌慌张张的我抱着吉它,踢着正步走到舞台中央—那里支着两只麦克风,还放了把椅子。
台下鸦雀无声,我放眼看去,一片黑鸦鸦的板寸头——都是和我一样的小兵,于是我就不紧张了,是真的不紧张。
敬了个军礼,我坐了下去。这些都是过场的时候安排好了的,军区宣传部的人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军礼,要知道台下不止是部队,还有不少军民共建的地方单位领导呢。
走了几个分解和弦,我的歌声便响了起来,通过麦克风经过扬声器传遍礼堂的各个角落:妈妈,妈妈,您还好吗?
您的来信我昨天已经收到啦,别担心,别难过,儿子在部队挺好的啊吃得香睡得好还长高了那妈妈,妈妈,要注意身体啊不然儿子在部队会担心的啊虽然我拿着枪天天站在哨位上但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家想着妈妈您啊妈妈,您知道吗,昨天我受到表扬啦,班长还说,明年我就可以放假回家看看妈妈啦。
噢妈妈啊妈妈,儿子一点也没觉得苦和累啊穿上军装,我也从没感到后悔过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尽对祖国的义务那……
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简直算不上是歌词,纯属于大白话,但我知道我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再也没有了那种感情。
结束的时候,我才发现泪已经流了一脸。雷鸣般的掌声中我站了起来,对着台下全体起立大力鼓掌的兄弟们敬了个军礼然后踢着正步下去了,同时脸红的想这次脸可丢大了,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淌眼泪……
但我下去后连里弟兄们都说好,还说自己也掉泪了云云,我压根就没信,肯定是这帮家伙安慰我,直到后来晓丹和我说了我才相信,她说她当时在台下也哭了,还说旁边连队的几个男兵当时就嚎啕大哭,还直叫妈妈妈妈的~~~结果我为咱们师争了荣誉,集团军的宣传队和军区文工团的一帮专业半专业的这次都出节目了,但我还是把他们比了下去——第一!!
当天师长就摆开了庆功宴——他不能不高兴,这可是有史以来咱们师第一次在汇演里这幺露脸,以前连前十名都没进去过。师长有些喝高了,一张黑脸红得发紫,拉着我的手连说感谢,然后就一再拍我的肩膀,把我打得生疼但还得站得笔挺,首长面前一个列兵功再大也不能放肆。
师长还拉着一帮首长和举着锦旗的我合影照相,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照片—在一帮身着将校尼的军官簇拥下,一个脸黑黑的小列兵齐胸举着大红烫金的锦旗傻呵呵的站在中间,笑得极其不自然,而且还露着一口大黄牙—我是四环素牙。
男人不识本站,上遍色站也枉然
开元棋牌
PG娱乐城
永利娱乐城
六合60倍
官方葡京
金沙国际
注册送888
澳门葡京
太阳城
新葡京
澳门葡京
澳门葡京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金沙国际
开元棋牌
澳门金沙
澳门葡京
银河国际
开元棋牌
大發国际
威尼斯人
PG娱乐
大发娱乐
英皇娱乐
官方开元
注册送18888
凤凰棋牌
赔率60倍
永利皇宫
开元棋牌
免费呦呦游戏
少女·网红·破处
反差女神外流
萝莉直播大秀
黑丝人妻NTR
免费呦呦破解